原标题:顺民的抵抗:被统治者的“三十六计”
原创: 读嘉出品 读嘉


文/苏则(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42 篇文章
本篇9257字,大约阅读时间为22分钟
引子:“沉默的大多数”与“弱者的武器”
说到专制的旧社会中的民众形象,鲁迅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描绘:统治者(“主人”)高高在上,不把底层当人看;而被统治者(“奴才”)一面很明白自己“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一面却在真正期望帮助他摆脱奴役的少数“傻子”出现之后,主动选择为虎作伥,告发此人向主子献媚,捍卫“咱们的屋子”——于是乎,主子在奴才的帮助下赶走了傻子,原有的奴役关系也得以“千秋万代”地继续下去。

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然而,文学表现往往不免夸张。在真实的古代专制国家的社会之中,像傻子一样勇于反抗的人固然是很少的,但真正积极地去做奴才、主动出手去维护专制统治的人,其实也未必占到民众的绝大多数。专制社会中最普遍的民众们,实际上更类似于王小波笔下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撼动统治者的权柄,他们确实属于顺民,但他们也并没有机会厕身于统治者的奴才之列,反而常遭到欺压。他们“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这些人在政客和官僚充斥的正史里拥有很少的话语权,但这些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却更加接近专制社会民众的主流。用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的话来说:
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①
而在这类人数上占很大比重的沉默弱势群体中,帝国小农又是特别典型的: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比较少见且极少成事;东亚大陆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往往是非农民阶级人士(著名的如前驿卒李自成、前捕快张献忠,属于帝国财政危机后“被下岗”的体制边缘人士,又如落第士人洪秀全与黄巢,实属官僚预备役部队)领导的流民暴动,而在这种暴动的过程中,安土重迁的农民又往往是被流民部队裹挟着、失去了私人土地和财产后去参与战争的(参考《流民暴乱》篇)。无论是在日常政治还是在非常规的战乱中,古代帝国的小农其实往往是扮演着被动、隐忍和失语(被代言)的角色。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正因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这些沉默的农民来说过于“奢侈”,太陌生了,所以斯科特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叛乱,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②斯科特把农民的这类反抗称为“弱者的武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我们下面就来利用他的学术观点,看看人类历史上那些顺民们(包括但不仅仅是农民),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国家(或者帝国)机器的,而他们抗争的国家(或者帝国)机器,又如何深远地影响甚至塑造了他们。
一、偷懒破坏:顺民的消极怠工
对于散沙小农,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刻板印象:“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么苛刻的自然条件下谋求生存,他们一定是非常勤劳辛苦的——然而,在历史的很多情形下,这个结论并不能够成立,我们不妨来看看匈牙利诗人盖拉·伊利埃斯(Gyula Illyés 1902 - 1983)对他童年生活的一段回忆——他在20世纪初匈牙利草原的一个大农场里长大。在那里,农场帮工的工作没完没了而且有很长的工时,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都是如此。伊利埃斯回忆,这些农场工作人员们的工作方式“就像农场里牲畜的反应一样”,“是以缓慢的手脚完成每一个动作”,伊利埃斯描写洛卡大叔在工作时抽空抽烟,是“像乌龟一样从容”地填装他的烟斗,而当“他划火柴时,就像他手中的火柴是取火的最后一种可能的方式,并且整个人类的命运就依赖于它了”(Illyés1967:1267)。这种消极怠工的方式,可以被看作是对地主和工头提出的过度要求的一种反抗形式,伊利埃斯把它表述为“一种本能的防卫”。③

农场帮工们在为农场主工作时放放水,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他们毕竟不是农场的所有者,他们的工作也不能够使得自己直接获益,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作为名义上土地所有者的普通农民们,也会用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消极怠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最著名的当然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例子。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止于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指的是斯大林等人推行的大规模建立农业集体经济的政策。在这过程中,苏联政府自上而下,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推行集体农庄,在集体农庄内实行土地、农具、牲畜的集体所有制,并为这些农庄提供种子、机器和拖拉机、发放优惠贷款④。
这看起来是推进苏联农业机械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利国利民”之举,土地牲畜由个人所有改为集体所有,并没有完全取消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却隐藏着苏联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并增大国家粮食收购以为快速工业化积累资本的雄图。粮食收购数量随农业集体化进程激增。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计划经济管理局的资料表明,全苏1927-1929年粮食收购数量逐年增长,1927年为520万吨,1928年为635万吨,1929年为1362万吨,是前一年的2.5倍⑤,因此一开始就遭到了农民的抵制。苏联于是采用强制方式继续推进,“中央黑土区的乌斯曼区和阿年区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从逮捕开始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搜查,进行财产登记,所有不愿意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都遭到逮捕,被捕农民中有80%是中农和贫农”,于是,“十天之内,该区集体化比例由原来的26%提高到82.4%”⑥。

苏联工作人员征收隐藏在墓园的粮食。斯大林指出,为了“从农村汲取货币积累”,必须“规定期限,让农民最大限度地加速向国库支付所有的一切……争取提前交付所有的欠款”……要求粮食收购人员“不实现根本转折就留在当地别回来”,各级组织领导人都要指定任务量,工作不力者将被“立刻清除”。
苏联农民们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仍然用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给予了回应。苏联情报档案显示,在集体农庄,一些“庄员对集体农庄的牲畜、财产和农具进行哄抢,大批庄员退出集体农庄去打短工,留下的人也拒绝参加劳动”⑦;而农民中的妇孺,则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通过“吵闹”和“淘气”表示抗议:“在‘富农帮凶’中,村妇发挥了极大作用。大多数群体暴动的规模都是在村妇的参与下由小变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30 年的(苏联农民)群体事件中有3700 多起的参与者都是村妇,在其余的几千起群体暴动参与者中,村妇也占多数。
村妇们的反抗都是有组织进行的,村妇们的行动完全得到了家里男人的支持,男人往往把女人推到前台自己躲在后面出谋划策,因为女人们‘能吵吵,更能据理力争’,而且,‘女人承担的责任小,政府不能把她们怎么样’,村妇也禁止男人参与事件,让他们‘别插手,这是女人们的事儿’。事实证明,(苏联)政府对村妇的惩治明显心慈手软,尽量依靠说服教育来平息群体事件,经常向村妇妥协,只有很少一部分带头闹事的遭到逮捕,武力镇压的比例极低。因此,村妇的反抗行动更有恃无恐。乌克兰安东诺夫卡村的一名村妇说,‘我们谁也不用怕,他们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中伏尔加河红军村的一名村妇也告诉大家“就是不把教堂的钟给他们,看他们怎么办’。‘富农帮凶’中还有很多年轻人,为了逃避惩罚,他们怂恿小孩子去纵火,因为侦察机关经常认为这是小孩子‘淘气’而不予追究。”⑧
这种看似无理取闹、对农民自己毫无好处的消极怠工和财产破坏,其实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抗战。斯大林写给《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一封信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斯大林在这封信中写道:“你那个地区(不仅仅是你那个地区)受人尊敬的谷物生产者已经开始了‘意大利罢工’(ital’ianka),怠工!而且他们并不认为使工人和红军没有面包吃有什么不对。这些怠工是平静,从外表看是没有危害的(没有流血),但实际上是‘静静’地反对苏维埃的战争。一场饥饿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⑨斯大林为此震怒,他一方面谴责农民阶级思想落后,劣根性不改,贪婪、自私、愚昧、粗野,一面认为农民的做法是要颠覆苏维埃国家,因此必须加以惩罚。

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到1934年,斯大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场战争是极为严酷和得不偿失的。学界估计的死亡人数在较为保守的三四百万到两千万人之间。而“在死亡数字背后,还有比十月革命以后的国内战争更多的社会破坏和反抗。数百万人逃到城市或边疆,声名狼藉的内务部劳改局(古拉格)人员大大扩充,在许多农村出现了公开反叛和饥荒,整个国家超过一半的牲畜(和役畜)被屠宰。”小农们利用消极怠工和胡闹破坏的方法,使得斯大林的雄心壮志落了空。斯科特指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并没有实现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它们明显没有能够为城市工业化的工人增加谷物产量或生产更便宜、更丰富的食品。它们没有如同列宁所预想的成为技术上有效率和创新的农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苏联)每公顷的粮食产量一直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和革命前达到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一些国营农场或者展示型项目的产量较高,但那是用巨大的机械、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投入作为代价的,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算的。⑩
通过消极怠工和胡闹破坏的方式,回避国家机器对自己的掠夺,也是东亚大陆帝国治下普通民众的常规操作。不但如此,这种现象几乎和帝国历史上每一次官方对社会的经济控制的加强相伴而生。在汉武帝时代,桑弘羊通过盐铁官营的方式使西汉政府得以专自然资源与手工业之利,于是被官府征用的手工业者选择制造连草都难以割动的劣质农具搪塞(《盐铁论·水旱》);汉武帝采用算缗令和告缗令征收民间社会财富,中产以上家庭几乎全部破产,平民们的应对策略便是消极的抵抗——他们从此开始过度消费,得吃就吃,得喝就喝,谁也不再踏踏实实经营买卖、蓄藏的事业了(《史记·平准书》);王莽推行土地国有的“王田制”,农民“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于是“民弃土业”,“闭门自守”,不再努力耕作(《汉书·王莽传下》)。
帝国顺民破坏怠工的畸形行为模式在东亚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普遍又扭曲的现象:自残避役——破坏自己的身体来躲避帝国的赋税差役。在帝国财政极大扩张的宋神宗—王安石时代,为了躲避要求平民承担军事义务的保甲法,部分开封民众的选择竟然是截指断腕(《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这种现象贯穿东亚大陆中古以来的各个世代,在所谓盛世的贞观之治也仍然存在。《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记录,隋朝末年赋役繁重,人们往往自残身体,称之为“福手”、“福足”,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仍然存留这种风气,所以他在贞观十六年下制令: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而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在某些人眼中只是打击富民,但非常关爱贫民的朱元璋大帝的治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福建沙县平民罗辅等十三人相约断指,原因是:“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大诰续编》)所谓“没用”意即断指之后,便是废疾之人,成为所谓不承担差役的“畸零户”,由此可以逃避各种差役。爱民如子的朱元璋大帝当然不忍心民众受此折磨,于是进一步迫害这些民众。万历年《新昌县志》记载“洪武初,遍捕断指者”,明代辽东档案记载:洪武二十五年从直隶、山东、陕西、山西、广东等省有许多为“剁指事”充军辽东各卫,其身份均为乡民(赵克生《历史上“断指”现象探源》)。

“避役”后来也成为汉语界“变色龙”的学名,变色龙的生理特性源于对险恶自然界的适应,帝国顺民自残避役的做法也是如此。《南齐书》记录,齐高帝时,竟陵王萧子良上疏痛陈时弊,提到∶“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
二、用脚投票:顺民的自我放逐
顺民消极抵抗的另一种常见方式,则是自我放逐——弃耕抛荒,到蛮荒之地开始新的生活。东亚大陆有非常悠久的“隐士”、“逸民”的文化传统。和西方出于宗教追求的理由而主动归隐的隐士(hermit)传统不同的是,东亚大陆的隐士传统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指向了对国家机器的逃避。陶渊明著名的《桃花源诗》中的几句——“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显然指明了这种“避秦”、“免税”的理想。
而在东亚的中央帝国对民间社会的经济汲取过于强大时,普通民众往往隐蔽山泽,逃避赋税。例如在王莽推行“大政府”经济政策,搞得“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动辄触碰政府禁令,没有办法正常耕作),“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时,民众们就“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官吏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于是“浸淫日广”,“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汉书·食货志下》),达到很大的规模。

先秦《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东亚南部、西南部一些所谓的山野蛮族,正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形成的,他们在种族血统上未必和附近平原上的普通民众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只是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在南朝陈代,福建豪侠陈宝应父子本为汉人,而效法蛮族生活习惯,穿草衣,梳椎髻、采用箕坐(两腿张开坐着,形如簸箕,在汉文化中是不礼貌的坐姿),成为了蛮族的首领⑪。
又如,“在9世纪,中国官员就报告说,在中国西南地区被称为尚(Shang)人的族群最早的时候本来是汉人,后来逐渐与‘西南蛮夷’混合起来。后来被称为山越的族群似乎最初也是普通的民,为了逃避纳税而逃亡,从而成为蛮夷。14世纪早期官吏的报告将他们看成是危险且无序的,但是没有任何指标表明他们与那些纳税且被统治的人在种族和文化上有任何区别(更不要谈起源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生活在国家范围之外,他们逐渐成为山越族。”⑫

山越,三国时期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交界处附近山区生活的部族统称。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和山越》:东汉末期更有很多人民逃避赋役,匿居深山,这些人和原来居于山中的人民一起生活,当时也不加分别都称为山越。
像这类例子,帝国民众从“文明社会”,转入深山大泽,成为“逸民”、“野人”,这究竟是不是一种文明的倒退?斯科特研究东南亚高地部落民的历史,得出了极富启发性的观点。斯科特认为,与其把这些部落民视作是文明水平低下的野蛮人,不如“把这些山地居民看作是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在过去2000多年中,他们成功逃避了谷地国家项目的压迫——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这些民众其实是通过“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逃避帝国的统治和剥削。例如,在《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的描述中,丹杨郡山越面对帝国官吏,手持兵器,逃亡山野之间,“白首于林莽”,难以控制,其中还包括所谓的“逋亡、宿恶”——所谓的“逋亡、宿恶”,其实正是逃避赋役与避罪的汉地民众。而诸葛恪这类吴国官吏攻击他们,本意也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兵源和赋税人口⑬。
出于这种目的,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自我野蛮化”选择的地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适合于逃避国家管理。“实际上,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他们分布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的流动性、耕作习惯和亲属结构,他们适应性极强的民族认同,以及他们对预言中千年领袖的热衷,这些都有效地帮助他们避免被统合入国家体制,也防止他们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他们大多数人要逃避的国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国王朝。逃避的历史可见于许多山地传说。尽管公元1500年以前的资料还有些推测成分,但这之后的文献足够清楚,包括明清时期政府经常发动针对山民的战争,以及19世纪中期中国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起义高潮,导致数百万人寻求避难所。此外关于逃避缅甸和泰国国家发动的劫掠奴隶的行为记载也同样丰富。”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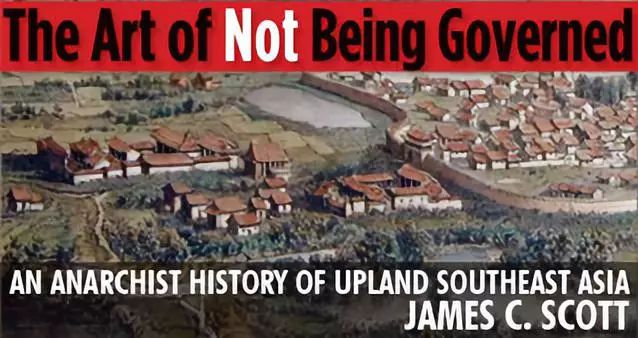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当国家弥漫在所有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在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
东亚大陆帝国顺民自我放逐的极端方式,正是斯科特所谓的自我蛮族化。这种过程在推崇汉化、认为帝国就是文明中心的传统史观中很少体现,但偶尔流露的信息,仍然以其极为生动的真实感给我们以启发。如《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提到:“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侯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边塞上给人做奴婢的人十分愁苦,想要逃走的人很多,听说匈奴那里生活轻松快乐,只是哨兵看得很紧,没有办法。然而也还不时有逃出边塞的)。
相关史料中,最精彩的也许还是明代谢肇淛的笔记杂著《五杂俎》。作者提到当时帝国边境民众往往逃入胡族领地的现象,评论说:他们和胡族的饮食语言是相通的,而中央帝国的赋役繁重、文网周密,不如胡人社会来得简便轻松。胡人社会中虽然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制度,但是“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当部落迁徙转移驻地,胡王与其妻妾子女都能够亲自工作,所以民众也能同心协力,敢死不顾。在战斗之余,民众逐水草畜牧,可以自便,“真有上古结绳之意”,而一旦进入帝国境内,官吏就可以拿着鞭子鱼肉他们了⑮——这就是他们自我放逐,选择成为蛮族的原因。
三、中央帝国对东亚顺民的塑造
今天我们介绍了中外历史上集权帝国(或国家)顺民在面对力量相对自身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国家机器时两种典型的抵抗方式:消极怠工和自我放逐。毫无疑问,它们都不是什么能够根除问题的手段,偷懒破坏并不可能在事实上扭转帝国集权和社会萎缩的堕落倾向,逃之夭夭也不能,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大概并不会想要过分苛责这些弱小的被统治者,反而可能产生一丝同情——他们至少没有为虎作伥,助长过度强大的帝国(或国家)机器的暴行。
与此相反,我们会对那些认为这类消极抵抗的行为体现了民众愚蠢懒惰、不可救药、活该受人统治的统治者们嗤之以鼻——那些顺民们“不思进取”、“不服王化”,恰恰是他们抵抗帝国剥削的隐微方式,这是被统治者们逼出来的。在明代文人冯梦龙编纂的笑话故事集《笑府》中,有一则有趣的“遇盗”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些消极抵抗的心态类似:
有个贼闯入一个穷人家里,四处掏摸翻检,一无所获,于是非常气愤地往地上吐了口口水,打开门就打算离开。穷人在床上看到了,唤道:“贼啊,请你关了门再走。”贼说:“就因为你这么习于懒惰,所以才挣不下一个家业来。”穷人反唇相讥道:“你让我挣家业。我挣家业难道让你白白偷走么?”(“我做人家与你偷么?”)⑯

在这个笑话中,贼和穷人的关系,非常类似帝国和那些消极怠工、抛耕弃田的顺民的关系:顺民为了抵抗帝国“无微不至”的掠夺和剥削,干脆彻底放弃了勤劳致富的道路。这个思路,和汉武时代的工匠们在盐铁官营之后干脆粗制滥造、滥竽充数是一样的,和俄国众多农民在听说要把牲畜和器具集体化后就选择杀牛宰羊、大吃大喝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与其说是这些顺民们生而懒惰、好逸恶劳,不如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在帝国统治下不得已而为之。
顺民们的自我放逐也是一样的道理,人谁不怀故人、怀故土?谁不希望和身边的亲友守望相助、共谋幸福?然而千百年来为数众多的古代大陆帝国平民北走胡、南走越,非要在并不熟悉,生活水平也未必有多高的异域筚路蓝缕、白手起家,难道真的是毫无缘故的吗?这些人其实可能还是顺民中相对更有骨气和自主意识的人,而伴随着他们的自我放逐和自我蛮族化,帝国中更为消极和懦弱的人逐渐沉积了起来。
可以说,在根源上塑造了帝国顺民逃避被动的形象及其行为模式的,正是帝国本身。我们试一试翻阅古代中央帝国的民间谚语、俗语,可以看到大量在其他文化圈中相对较少见到的主张消极逃避的条目,正是这种塑造的明证。例如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经明清两代文人不断增补而成的儿童启蒙书《增广贤文》中便有一连三条名言云: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而在这三条自甘懦弱、主张逃避的“劝世良言”之后,则是与这几条俗话语意相连的“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畏惧法令就可以天天安乐,欺瞒公家就会日夜忧虑)——这在某种意义上,正解释了这些“民间智慧”形成的缘由和它们畏惧和逃避的对象:“公家”(帝国)的法令。用《增广贤文》中的比喻来说的话:“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官法足以摧毁无比坚强的人心。

《增广贤文》,东亚帝国的成功学入门
《增广贤文》的作者们和受众们虽然有时认可财产的可贵(如认为“礼义生于富足”),但他们往往倾向于把金钱和地位权势相连(例如“有钱能说话,无钱话不灵”、“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并更多地相信富贵其实来源于运气:“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中只有如许财,丝毫不可有闪失。”另一方面,事实经验又往往告诉他们,面对帝国力量(官府),财富是靠不住的,反而可能因此招致更大的灾祸和忧患:“贫莫与富斗,富莫与官争”、“欲多伤神,财多累心”、“富贵多忧,贫穷自在”。
在一些真实的历史里,这些顺民真的会为了躲避官府的压榨而放弃个人财富。例如,在北宋早期的基层社会,官府要求比较富有、人丁兴旺的家庭来负责提供义务的差役工作,但这些差役经常因为被官吏敲诈而倾家荡产,于是为了躲避差役,民间开发了五花八门的办法——“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以苟免沟壑之患”,让母亲改嫁,亲族分居以减少人口,放弃田产以免被划为“上户”(富裕之家),甚至还有老人自尽的极端案例。⑰
这种社会环境的自然结论,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民间智慧——被动地听从“天命”的摆布而不思进取: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莫怨天来莫怨人,五行八字命生成。”
“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另外就是我们同样非常熟悉的“知足”、“知止”的民间智慧:
“知足常足,终身不辱;
知止常止,终身不耻。”
有些人把这类“知足常乐”的东方民间智慧和古罗马斯多噶学派(Stoicism)摒弃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精神相比附,其实,产生这两者的动机和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斯多噶派的哲人们,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是“把财富,人间的显赫、痛苦、忧伤、快乐都看作是一种空虚的东西”,他们“埋头苦干,为人类谋幸福,履行社会的义务。他们相信有一种精神居住在他们心中。他们似乎把这种精神看作一个仁慈的神明,看护着人类。他们为社会而生;他们全都相信,他们命里注定要为社会劳动;他们的酬报就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更不至感到这种劳动是一种负担。他们单凭自己的哲学而感到快乐,好像只有别人的幸福能够增加自己的幸福。”⑱这是精神富足者对社会事业的主动承担。
而宣扬 “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的东方民间智慧,并不是出于多么高深的哲学理念,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可能遭遇的现实个人耻辱而已——说到底,仍然不过是东方哲学里常见的“逃避”二字。
但这并不是说,东方人就一定天生庸俗堕落。一方风土养一方人,一方的社会结构培植了一方的民众精神和民间智慧。我们对照前两节所揭示的事例,可以看到这些看似毫无道理的自甘贫弱和消极逃避,甚至自残躯体的做法,实际上正是顺民对抗帝国的对策。在古代东亚大陆诸帝国的统治下,努力致富和上进的人,反而容易成为暴君和腐化官吏们眼中待宰的肥羊——例如沈万三这样的富商。正如冯梦龙《笑府》里遇贼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果“做人家”只是“给人偷”,那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去冒险创业拼搏呢?古代专制帝国对社会和民众的单向压制和逆向淘汰,最终塑造了散沙顺民消极懦弱,不图进取的历史形象。

电影《七武士》中,农民出身的“武士”菊千代在他的战友面前袒露他对他非常熟悉的农民的看法
注 释
① 詹姆斯·C·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 译林出版社, 2011: 2.
② 詹姆斯·C·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 译林出版社, 2011: 2.
③ 转引自彼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④ 吕卉.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27-1939)[D]. 吉林大学, 2010.
⑤ 吕卉.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27-1939)[D]. 吉林大学, 2010: 72.
⑥ 吕卉.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27-1939)[D]. 吉林大学, 2010: 70-71.
⑦ 吕卉.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27-1939)[D]. 吉林大学, 2010: 84.
⑧ 吕卉.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27-1939)[D]. 吉林大学, 2010: 73-74.
⑨ 转引自詹姆斯·C·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53-254.
⑩ 詹姆斯·C·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54-255.
⑪ 《陈书》三十五,列传二十九: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
⑫ 詹姆斯·C·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45.
⑬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丹杨山越)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
⑭ 詹姆斯·C·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2.
⑮ 明谢肇淛《五杂俎》论边民之入胡: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王荆公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者,此类是也。
⑯ 冯梦龙《笑府》遇偷:偷儿入一贫家,遍摸一无所有,乃唾地开门而去。贫汉于床上见之,唤曰:“贼!可为我关了门去。”偷儿曰:“你这个人叫我贼也忒难。”一说:唤贼关门,贼笑曰:“我且问你,关他做甚么?”亦有味。旧说云:“贼可替我带上了门。”贼曰:“是这等贪懒,所以做不得人家。”贫汉曰:“我做人家与你偷么?”
⑰ 《宋史·食货上五》: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
⑱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原标题:《顺民的抵抗:被统治者的“三十六计”|读嘉》
阅读原文 游戏网
| 相关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