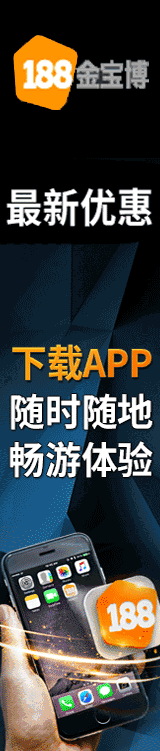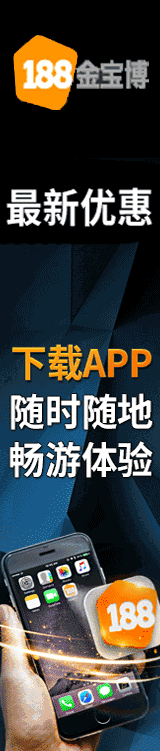原标题: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

一部佳作
阿诺德·汤因比曾写到,“在世界与西方长达四五百年的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然而,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到11世纪的数百年间,欧洲还远不足以对世界造成什么打击,恰恰相反,它却在四方强邻的蹂躏下喘息呻吟,危在旦夕。对于这种戏剧性反差,人们自然将目光投向所谓“欧洲的诞生时期”,这也构成了《罗马帝国的遗产》(TheInheritanceofRome:AHistoryofEuropefrom400to1000)一书的主题。
作为“企鹅欧洲史”(ThePenguinHistoryofEurope)承上启下的关键部分,无论从长达六百年的时间跨度来说,还是从囊括三大洲的空间范围而言,《罗马帝国的遗产》都展现了克里斯·威克姆(ChrisWickham)重新阐释由古典向中世纪过渡阶段的雄心抱负。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诚如菲迪南·罗特(FerdinandLot)所言,“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可能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呈现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最令人震颤的景象之一。”
对于罗马帝国的覆灭,人们的看法往往陷入两种极端:出于对中世纪的偏见,古典文明的衰亡便充满道德批判色彩;而近代西方的兴起,又使许多人过高地估计了中世纪欧洲的发展。纷繁复杂的学术观点,便如同摇荡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循环往复。
克里斯·威克姆当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在卷首即开门见山地反驳了两种宏大叙事对理解中世纪早期的误导,即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而这两者恰恰是当今许多史学类著作的共性。19世纪初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真实图景被民族起源和身份认同的叙事所裹挟,这导致人们从横向上误以为欧洲的认同是由来已久的,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今天的欧洲地图对于理解中世纪早期的地缘政治不仅少有助益,甚至会产生误解。与此相对,现代性的叙事从纵向上割裂了中世纪最初数百年与罗马世界的延续性,对于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而言,中世纪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衬托前两者的光辉,至于它自身似乎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某种“异类”。
当然,从20世纪后期开始,长期的偏见在西方学界已得到了显著纠正,肇始于彼得·布朗(PeterBrown)的“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传统使人们相信,古典文明在帝国晚期经历了深远的蜕变,中世纪早期也远没有那么不堪。正是出于上述种种关怀,《罗马帝国的遗产》不仅以其宏大的时空架构成为各卷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同时它精湛的分析无疑为我们观察中世纪欧洲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视角,毕竟在中国学界,扭转对中世纪的偏见依旧任重而道远。
比较视野下的解释框架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由于总是和“黑暗时代”或“封建主义”等描述相联系,长久以来显得声名不佳,这种现象并不难于理解。《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是雅克·勒高夫的最后之作,他在其中极富洞见地说“新时期的一种观念总是反对前一时期的观念,后者总被认为是黑暗的阶段并理应让位于光明。”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言,中世纪的“污名化”尤其如此。然而,如果认为威克姆的《罗马帝国的遗产》旨在全面“洗白”中世纪,那就大错特错了,批判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叙事本身并非目的,对中世纪的过分高估和人为贬低,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因而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对历史采取“事后诸葛亮”(原文是 hostilitytohindsight)的目的论完全无助于正确认知,将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使历史解释框架更为精致、复杂才是作者的初衷。
那么,作者不带“目的论”的目的完成得如何呢?至少从各篇和全局的结论来看,完成得相当成功。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威克姆使用的许多方法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事实上,早在2005年出版的《构建早期中世纪: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FramingtheEarlyMiddleAges:EuropeandtheMediterranean,400-800)一书中,威克姆就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结构分析和比较视野运用于早期中世纪史的阐释。
欧洲从罗马来
这一特征在《罗马帝国的遗产》中得到延续和发挥,这首先体现在他将考察的时段向下延伸到公元1000年,虽然威克姆也承认这种划分有忽略各地多样性的不足,但是从总体而言,在政治变迁的意义上,以公元1000年作为中世纪的分水岭依旧是站得住脚的。关键在于,800至1000年这段时期正是加洛林王朝的霸权崩溃、地方贵族崛起和封建主义成型的阶段,站在11世纪的门槛上能够对公元第一个千年欧洲的政治变迁做整体的回顾。
更重要的是,虽然属于“企鹅欧洲史”系列,但是威克姆也将地理范围扩展到包括西亚和北非在内的前罗马帝国疆域,尤其拜占庭和阿拉伯诸帝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如果说威克姆重视中世纪早期西欧三巨头——西哥特人的西班牙、法兰克人的高卢和伦巴第人的意大利——之间的差异的话,那么,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加洛林王朝(西欧)、拜占庭帝国(东欧)和哈里发国家(西亚与北非)之间的比较研究,丝毫不亚于对前者的重视。威克姆相信,在统一的罗马帝国解体后,地中海世界的各政治体走上了既迥然有别又保留某种共性的道路,如果没有加洛林王朝和东方诸帝国的比较,便不会清晰地发现,税收体系的延续如何在拜占庭和阿拉伯维系了强势国家(strongstate),而税收体系的崩解和土地日益成为权力的来源,如何在西欧造就了弱势国家(weakstate)以及后来的封建主义。这种比较研究揭示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在共同传统的背景下分道扬镳的深层结构,这也是本书命名为《罗马帝国的遗产》的重要原因。
《构建早期中世纪》侧重于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宗教文化领域则相对薄弱,《罗马帝国的遗产》弥补了上述缺陷。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和信仰的内容虽然散布于各篇,但实际上所有相关章节仍可单独析出组成连贯的整体,可谓“形散神聚”,也从侧面印证了中世纪早期与古代晚期的延续性。
2016年,耶鲁大学出版了威克姆的最新力作《中世纪的欧洲》(MedievalEurope),这次他将整个中世纪作为考察对象,涉及罗马在西方的继承者、东部的危机与转变、11世纪开始的经济扩张、中世纪盛期的政治重组和货币、战争及死亡等问题,如何在不足300页的正文中概括一千年的历史,无疑是一项挑战。这部书和《构建早期中世纪》、《罗马帝国的遗产》构成了威克姆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三部曲”。
可贵的多样性
支撑上述政治与文化变迁的深层结构,隐藏于400至1000年的社会与经济体系之中。多样性历来是欧洲的重要特质,它不以罗马帝国的强弱盛衰为转移,它是中世纪各个阶段发展趋势的基础,近代以来欧洲的迅速崛起,也同样受益于这种多样性,实际上,它也是欧洲历史丰富而迷人的核心要素之一。为了更接近中世纪早期的真实情况,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多样性,正如书中强调的那样,作者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比,而不是归纳,目的就在于尊重这些差异性并指出其意义。对于中世纪早期这样剧烈变动的时期来说,多样性的意义首先在于,任何趋势都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地定性为进步或者倒退,但由于史料的匮乏,定量分析又很难实现,这种情况下多样性的作用便凸显了,它至少可以不断修正我们对某些趋势的把握。
罗马帝国的分裂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原先统一的地中海经济体变得支离破碎,5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间,西地中海的贸易路线无疑是衰落了,由于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和西西里岛,而这两地恰恰是罗马最大的粮仓,对海上贸易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是问题在于,东地中海世界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稳固统治,其贸易网络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更为繁荣密集,所以整体而言地中海贸易网络依旧存在,只是范围缩小了而已。7世纪前期拜占庭的衰退和随后阿拉伯人的扩张,再次导致地中海上的贸易跌至谷底,但是很快在8世纪中叶再次复兴,虽然规模和繁荣程度不可与帝国时代同日而语,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地中海贸易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悄然变化:随着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复存在,由官方主导的贸易网络逐渐被各地区间自发交换的贸易路线所取代,简而言之,8世纪的地中海贸易虽然不如4世纪以前那样声势浩大,但却变得更为市场化,也更具有商业活力。
“黑暗时代”的污名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的内陆地区,差异性同样使我们对农业社会的图景做出某些修正。中世纪早期的农奴制,无疑为“黑暗时代”的污名增添了合理性,无论这种机制在当时社会中是出于多么不得已的安排,它在今天的现代价值观念中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是问题在于,过去我们认为是欧洲普遍现象的农奴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典型,甚至可以说只是极少数地区的常态。威克姆通过对帕莱索(Palaiseau)、古尔斯多夫(Gaers-dorf)和吕菲阿克(Ruffiac)这三个农民社会的比较研究,揭示了领主与农民群体以及农村社会内部的不同关系,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业社会,使得西欧很少有某个地方能够削足适履地符合人们对农奴制的想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奴制在中世纪的欧洲无足轻重,只是对农奴制全盛时期的认知存在错位。诚如威克姆总结的那样,公元500至800年间西欧贵族的权势可能是相对最弱的,与之相对的是,地方社会的自治程度相对最强。其原因可能要追溯于前面提到过的“弱势国家”,统治者财富的来源由税收转向土地,的确削弱了国家政权整体的控制力,但是当时的经济结构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领主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时期的领主而言,他们的财富既不能与罗马帝国时期的前辈们相比,而他们对乡村社会——实际就是对人——的控制力又远不如他们的后代们。这样反而形成了农民的“黄金时期”,究竟是做丧失自由但至少能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农奴,还是做不得不为生计和收成而操劳且有破产风险的自由农,这个问题至少在10世纪以前还是有选择权的。伴随着11世纪的经济扩展和人口增殖,农民在这类问题上选择权逐渐丧失,以至于后来这已不再是个问题,农奴制的全盛期便到来了。
现在回过头重新审视中世纪早期欧洲的趋势,尤其考虑到上述多样性,就很难再给这个时期武断地贴上“黑暗时代”的标签了。必须承认这数百年中存在着种种衰退和崩溃,但远不是从前所想的那样不堪,一系列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发,虽然时常被内部混乱和外部入侵打断,但是终究步履蹒跚地走出晦暗。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有其自身的闪光点,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是被点亮的而非照亮的,只不过点亮之后,仍有许多部位处于阴暗之中。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McCormick)很好地总结过这种转变:早期中世纪已经不再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黑夜,它更像是一个漫长的清晨,为后来的发展积蓄着基础与活力。游戏网
责任编辑: